方立天
1933年3月3日生于浙江永康
2014年7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早报记者 许荻晔 发自北京
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宗教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和中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方立天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7月7日9时2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方立天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7月11日上午9时进行。
三个转折点
方立天1933年3月3日生于浙江永康。他曾总结,一生中有三个重要的转折点:1949年、1956年及1961年。
1949年方立天初中毕业,次年来到上海,在财政系统的干部学校(华东税务学校)学习,念了几个月就留校工作,后被调入马列主义教育室当助教,讲中共党史、联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四门课程。被赶上阵的方立天只得先去复旦听相关课程,回到学校再现学现卖,也颇受学生欢迎。
相比1949年的革命锻炼,1956年则是学术大门的打开。这一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在职青年报考高校,方立天不顾校领导反对,以同等学力报考了北大哲学系。
“我考试前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根据我的条件怎么准备这次考试。首先政治我没有什么问题;历史、地理,我把高中的课本都拿来系统地学了一遍;语文,我估计题目就是鼓舞大家前进,弘扬集体主义精神这些方面的。我准备的题目和后来考试的题目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已经有了腹稿。最大的问题是要考数学,数学要作为参考分。补习高中的数学我是来不及了,不过我考虑初中的题也会出一点,我要是把里边初中的分数拿下来就可以作为参考。所以我就把初中的东西复习好,结果好像差不多。”方立天曾总结自己如何以初中学历考进北大。
进入北大被他看做自己的学术新起点:“在中国哲学领域,冯友兰先生亲自为我们讲授了 中国哲学史 ,张岱年先生生前对我更是耳提面命,多有教诲。在佛学领域,汤用彤先生和任继愈、石峻先生都曾给我以直接的教导和影响。此外,陈寅恪、陈坦、吕澂等先生的佛学著作,是我案头不可或缺的,也使我受益良多。”在从教50周年研讨会上,方立天回顾了自己的求学生涯。
1950年代后期,北大要求老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冯友兰特为1956级学生开设“中国哲学史”,而方立天正是56级2班的课代表,有较多接触、讨教老师的机会。他曾问冯友兰,怎样才能学好中国古代哲学,冯友兰回答:“要把中国古代哲学中好的东西发掘出来,加以继承和弘扬,那才叫本事。”
“这句话对我来讲有指明方向的意义,我这一辈子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学术研究的。”方立天后来总结。
五年大学,因为运动,上课时间不过两年半,但方立天在哲学系学习的同时在历史系听了一年多的课,还充分利用图书馆自学。相对当时对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要求,方立天属于不红不白的“粉红色道路”,为此遭到批判。1961年毕业时,他因为觉得留京无望,将志愿都填成了青海。而这一年之所以成为第三个转折点,是因为方立天意外地被分配到人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可以继续自己的研究,而不用改行教马列政治课。
“三年不出好文章就走人”
1961年的京城四校排名还是人北清师,人大地位最高,其教学规划需要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对老师的要求也高。以哲学史教研室为例,不仅要能通讲从先秦到现代的哲学史,还要有研究重点、专业分工。系主任对方立天说,三年不出好文章就得走人。
方立天报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向,这一断代的最大特点是佛教的传入和儒释道三教格局的形成,因其难度大,没有同事报这个方向,“我就说我来吧”,“我想三年拿东西,也就佛教有成果。”
但除了幼年浙中农村的民间宗教氛围,与大学时任继愈两个小时的辅导人民大学宗教学(佛学),方立天对佛教知之甚少,他意识到自己首先需要补习佛教知识。当时中国佛学院在法源寺开课,方立天向院系领导申请后前去旁听,亲聆大师传道,体察僧人的修持实践,副院长、学者周叔迦还亲自开书单,让其定期汇报。方立天曾回顾这8个月的学习收获:“第一是增加了佛教的知识,第二是了解了佛门的生活,对他们的人格和修养有了直接的体验。我对佛门有一个直接的、感性的认识。这样我对佛教的观察角度就不一样了。”
有说法称1961年的佛学为“险学”,而与方立天相交多年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楼宇烈认为此说不确。“当时任继愈先生就有几篇文章批判近代学者的佛教研究,毛主席看了之后还批示应该加强宗教研究。所以那一时期宗教研究虽然比较谨慎,但还是被重视的。像我1961年上半年还在农村,下半年就被调回参与编《中国哲学史》了。当然方老师能去佛学院进修,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方立天最初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从个案入手,从研究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佛教高僧开始,进入整个佛教历史。1964、1965年,方立天相继发表学术论文《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前者发表在《新建设》,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后者发表在《哲学研究》,“要不就不发,发就在最好的报刊杂志上发。”方立天曾回顾当时投稿的心态。
《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后来被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翻译转载,而据说解放后十余年来被《中国哲学研究》转载的论文仅有三篇。在当时的学术会议上,有老先生惊讶于方立天的年轻,“这时心里有很大的充实和满足。”方立天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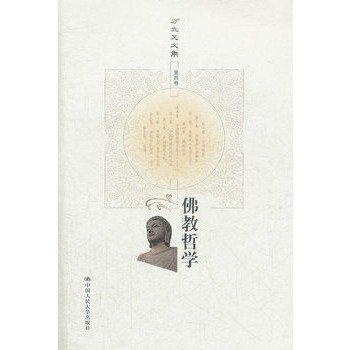
但虽然三年内写出了好文章,方立天还是不得不“走人”:四清运动开始,他被下放西山农场;“文革”开始后,他被下放江西,1972年回京并进入北师大,直到1978年人大复校,才回到人大,继续佛教研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方立天发表的文字有400多万字,论文350多篇,重要作品已被汇编为《方立天文集》,其研究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除了人物研究,方立天还着力整理佛经、古籍著作,他与石峻、楼宇烈等师友一起编辑的《中国佛教思想史料选编》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流行的佛教资料集,而其《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则获得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出版小组组长李一氓的高度评价,不仅为其撰写书评,还称之为古籍整理的典范。
1986年,方立天出版了代表作《佛教哲学》,对历时两千多年遍及五大洲的佛教文化的基本内涵做了深入浅出的概括,不仅受到学界、佛教界的推崇,也在非专业读者当中产生影响,历史学家周一良称之为“真正的佛教入门书”,获奖频仍。
方立天的佛学研究,一直在中国哲学史的大框架下进行,其《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自宇宙观、时空观、道德观、天人观、知行观等12个方面切入,从问题史的角度概括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张岱年曾力荐此书,认为写问题史难在广博、深切、精确人民大学宗教学(佛学),而方立天做到了“内容博雅、探索深切、诠释精确”。
2002年,穷15年之功、91万字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出版,被认为是佛教哲学研究史上的里程碑著作。楼宇烈评价方立天的研究:“近百年来,我们在学术研究方面唯西方马首是瞻,不能够很契合中国本土哲学和佛教的特点。方先生开辟了一条道路,让中国哲学和佛教学术研究重新回到中国文化的本位上来。”
“不争而争”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曾表示,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向张岱年请教推荐优秀的中年学者,张特别推荐了方立天。
对于自己的成就,方立天归因于“不争而争”:“搞学术需要很静,需要过寂寞孤独的生活。你对外界的很多物质诱惑都想去争取,就会影响你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去探讨学术。所以一些外部的名利你要想开一些,不要去争。但是我通过不争而争,争什么?争时间,争成果。”方立天2011年为人大宗教学研究生班讲话时说。
直到50岁时,方立天仍是一介讲师。1983年评职称时,方立天本来是副教授候选的第一名,但仍被刷下来了,他不明所以,后来有人告知原委:“领导找你谈话的时候,你应该表示感谢。你不感谢,听说还提了好多意见。”
1984年,中央提出要在全国重点大学的文科专业中,各选五个特批正教授,方立天因此破格提上了教授。但即便如此,两年之后,他才从不到30平方米的筒子楼,被分配到“一个又黑又暗又脏的三间里边”,“直到2005年”。
也因此,2006年以前发表的著作,方立天基本都是在人大图书馆完成的。“人大的图书资源滋养了我,我真诚感激人大图书馆对我的帮助。”在2011年从教50周年研讨会上,方立天还特地感谢了图书馆。
去图书馆是他在北大时养成的习惯,“在图书馆里看书,效率和在宿舍里是大不一样的。宿舍里的被子呀、枕头呀会影响你的思考;图书馆里看到的是书,是同学们在那里用功。所以我在北大就是一个背着书包去图书馆的学生。”
而到人大后,方立天每天早晨也还是和学生一起泡图书馆,直到关门闭馆。没评上副教授时,领导分析他将有几种可能:要跳楼、要调动工作、要消极怠工。结果第二天仍见他背上书包上图书馆,“学校就放下心了。”直到2005年搬家离开人大后,方立天才告别了人大图书馆。
最初在人大77、78级学生当中,有一个“跟学生在阅览室抢座的老师”的传说。而后随着图书馆条件的改善,教授可进大库看善本,方立天不必再跟学生竞争。而至于外界传说的“方立天专属书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主任魏德东向早报介绍,那是图书馆古籍小组办公室为他准备了一张书桌,但白天仍有工作人员使用,“我1991年跟方先生读书的时候,他一早去办公室放了包,然后去大库看书,晚上工作人员下班以后再来,那时候他给我们开会就用这张办公桌。”
“方先生是非常认真勤奋的一个人,天天要上图书馆,白天给他家打电话永远找不到他,晚上也回来得很晚。所以他能有这么丰硕的成果,我很佩服他这种精神。”楼宇烈对早报记者说。
但作为一名埋首书斋的学者,方立天也同时关注着社会发展,并在哲学、宗教中寻找对策。“面对方枘圆凿的现代政教关系,他悉心研究慧远的政教离即说并予以高度评价;应对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挑战,他探索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基于道德滑坡的现实,他研究佛教伦理的基本内涵与现代价值;他探讨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的归宿,是探求中国佛教哲学对解决当代人类困境的意义,这就是:关注人与自我的矛盾,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协调人与人的矛盾,维护世界和平;调适人与自然的矛盾,促进可持续发展。” 魏德东总结。
“思想本身不是抽象的理论,一定要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而现代社会,我们要充分发挥佛教净化心灵和社会的作用,对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不良现象,我们会经常提出批评意见。”楼宇烈介绍。
广义上,曾受教于方立天的桃李遍天下,但从他手中拿到博士、硕士学位的,不过五六十人。魏德东介绍,作为导师,方立天第一会尊重学生个人的学术志向:“不像某些老师指定课题给学生,方先生让学生做自己喜欢的东西,顺着学生的兴趣来指点。”
“第二则是让学生放手读书。那时候没有网络,他看到有价值的资料会裁下来,转给学生,还在边角上写 转某某、某某、某某阅,几月几日 。我那时候调皮,还把我自己名字圈一下,写 已阅 。搞得像传文件一样。”魏德东说。
此外,笔耕不辍的方立天还鼓励学生写作,希望学生通过写作来提高水准,在早期,他对学生的论文都是逐字修改,即便后来年纪大了,也都是通读全文提出修改意见。“做方先生的学生20多年,直到他临终之前,我见他都是毕恭毕敬。在他面前,你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太少了。”
7月6日上午,方立天曾陷入昏迷,多年的肺癌令他身体衰竭。经过抢救恢复稳定后,魏德东于晚7点离开医院,直到第二天早上接到噩耗。“我此前一直比较乐观,因为我相信方先生是非常刚毅的人,一直与逆境斗争,在1960年代他都能坚持研究佛经、守护中国文化,我觉得他怎么可能向命运屈服?但奇迹并未发生,我非常悲伤。”

声明:部分文章来自于网友投稿及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第一时间核实删除
